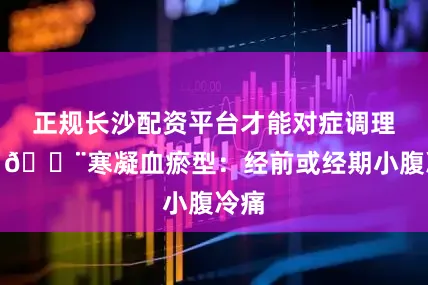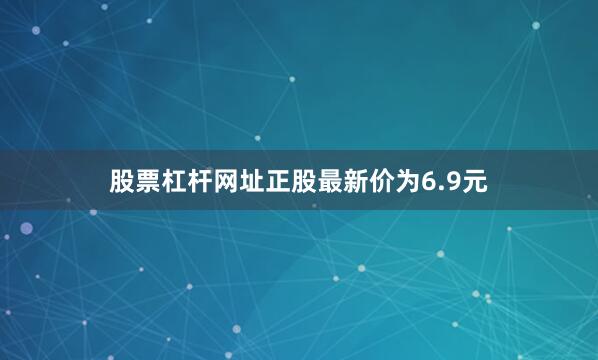当全球城市竞相构建创新生态,上海打造什么样的科创空间,才能促进科创的生长?
对科创企业来说,真正想要的科创街区,究竟应该满足哪些诉求?
从“被动等待”到“主动出击”
在上海大零号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,一处由老厂房改造的智能配用电房里,5米层高下,数百公斤重的精密设备正在运转。这里是“能优网”的办公所在地,也承载着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东科技成果转化的梦想。
“选择扎根大零号湾,首先是地理上的便利,让老师和同学能在教学、科研与企业运营间从容兼顾。”身兼能优网创始人的刘东说。大零号湾依托于附近的上海交大、华东师大,成为高校成果转化孵化基地,产业政策与高校资源一脉相承。
比如说,在政府的支持下,大零号湾与上海交大深度绑定。老师们手握校内科研成果,如果想要转化为产品,在市场上创业,需要经过校内三级答辩,通过“成果转化评审流程”。由学校先进技术产业研究院专门设立办公室,技转专员一对一对接,对教师成果转化项目进行评估审核,确保流程合规、过程高效。
展开剩余91%而校方邀请的第三方评估嘉宾中,有对行业技术了然于心的业内专家,有投资顾问类专家,也有大零号湾直接扶持的孵化器平台负责人。
“以前,我们就像守株待兔的农夫,只能等着高校的老师拿项目找上门来。”孵化器平台负责人坦言,这种被动的模式成效不高,不仅缺乏对项目成果的了解,而且当项目方来挑选场地时,往往已错失了最佳的孵化时机。
如今,与高校深度绑定后,大零号湾直接“前端介入”。校内哪些老师的成果正在走向市场,作为评估嘉宾,他们提前了如指掌。“我们的总经理本就来自交大,熟悉学校的科研体系和成果转化路径。”孵化器平台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。
当科研成果一旦通过校内的转化评审后,大零号湾长期驻校的专职办公人员马上与创业团队一对一对接,帮助初创企业代办一系列服务,涵盖工商手续、政策对接、融资辅导、员工培训等一系列烦琐内容。
而大零号湾园区也会根据评估等级,提供场地租金减免、装修补贴,落实各项扶持政策。这种模式的转变,让科技成果转化的周期大幅缩短。数据显示,自该机制运行以来,上海交大项目在大零号湾的就地转化率远超历史平均水平。
从刘东的角度来说,科技成果“躺在纸面上”是长期困扰高校的痛点。成果转化首先面临的不是来自市场的挑战,而是政策的束缚。
老师的校内研发成果,属于职务内发明,其专利能否作为企业的核心专利面向市场呢?两者有产权上的矛盾。
而现在采取的方式是:老师作为专利完成人进行专利转化实施,第三方评估确定其研发专利价值;学校把专利作为无形资产注入老师的初创企业;同时约定,未来企业发展中专利增值收益将按比例与学校分成,形成个人、企业与学校“三方共赢”的格局。
“从专利认定到经费使用,每一步都有章可循。”刘东认为,学校设立技术成果转化专员,专门对接教师创业的内外部事务,而大零号湾在交大派驻专员,更是让高校与园区资源实现“鱼水交融”。
这条科研成果转化路径,被老师们称呼为“阳光化”创业,即政策解绑、制度创新,鼓励老师们正大光明地运用科研成果,转化为产品,去市场上创业。
大零号湾作为科创街区,在“阳光化”渠道上,从前端评估到终端的软硬件供给,几乎全方位深度参与,让企业轻装上阵。
“阳光化”政策执行以来,上海交大共完成203家成果转化项目公司注册,其中98个项目落地闵行区(占比48.3%),近九成在大零号湾,总估值超500亿元。2024年,该区域9项牵头或合作完成的重大科技成果荣获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,有43项(人)项目获“上海市科学技术奖”,均占全市比例约1/5;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17406件,占全区近45%;省部级及以上创新基地60家,占全区75%;海外高层次人才1441人,占全区超90%。区域以高端装备、生物医药为主导产业,合计营收占区域总营收约80%。
“所以,不能把我们看成简单的园区一房东、二房东,或者科创空间场地的租赁方、运营方。”大零号湾副总经理叶隆说,“我们作为国有企业,承担的是科创中心建设的重大任务,做好从‘0到1’的高校成果孵化,才是目前的重中之重。”
建筑梦之队的未来尝试
那么,科创街区如果没有核心高校,又该怎么发力呢?
不久前,以“创新街区”为主题的SEA-Hi!论坛在张江科学城张江之尚创享中心举办,一些科创大咖聊到了他们心中理想的“科创街区”。
“我心目中理想的创新街区,应该是集建筑、艺术、人文、创新于一体的街区,是让科学家不仅想来而且还想留下来的地方。”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认为,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常常会与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喝咖啡,在一起交流、交锋,乃至交融,从而激发了更多的思想火花和创新灵感。
未来的创新街区不只有硬核的一面,更要让科学家们感受到艺术的氛围、人文的氛围,让大家的思维火花和创新灵感更多地喷涌而出。
也就是说,一个多元碰撞、有生活气息、人与人邂逅、科创灵感交融碰撞的“外部环境”,是科研人员特别喜欢的。
正因为看到这样的变化,已经久负盛名的张江科学城内,如今正在开发建设一个新项目:张江之尚。SEA-Hi!论坛还授予张江之尚“SEA-Hi!论坛特别基地”,期待这里成为更多跨界对话的发生地。
张江之尚前身为张江水泥厂,由上海地产集团携手张江集团共同打造,是上海市浦东新区“金色中环发展带”重点项目,打造三大先导产业的前沿创新高地。
此次张江之尚工业遗存的更新,汇聚了国内外12位知名设计师,如安藤忠雄、马岩松、雅克·菲尔叶、柳亦春、张斌等,他们每人选择一栋建筑或者建筑组群空间,从自身理解对未来科创街区进行诠释。
从水泥筒仓改造的文化艺术中心,到万米仓改造的科创方舟,再到链接未来科创展演的窑尾剧场,12位设计师的作品和而不同,充分考虑了科创人员的艺术、文化等生活服务的需求。
负责设计其中4栋办公楼的柳亦春接受采访时说,他在设计之初,一直观察着周边其他建筑的设计手法。南侧是马岩松由万米仓改造的科创方舟,北侧是安藤忠雄筒仓改造的园区文化艺术中心。
“我负责的4栋办公楼就是处于一个中心位置,反而承担了协调者的角色。”有鉴于此,柳亦春让建筑以一种弱化的姿态呈现在场地之上,用轻盈、纤巧、带一点工业理性的方式,与周边大尺度、粗犷的体量形成互补和统一。
一群跨国设计师联合组成的梦之队,在这样一个位于上海浦东张江地区、距离上海市中心约30分钟车程的老水泥厂的基础上创造空间的无限可能,将占地117,000平方米的工厂改造成一个科创新园区。它能够容纳超过500个研究机构、企业孵化器、初创公司、技术中心和服务平台。
张江之尚在打造科创街区时,如此强化历史空间的独特性,强调未来科创街区的公共性,突出艺术与文化的氛围,也是上海走在前沿的尝试。
“主要目的是促进那些跨界的、非正式的交流,激发科学家们的创造力。”张江之尚项目负责人彭晖说,50%的配套室内外空间将被预留用于展览,包括“科技+艺术”“文化+艺术”等一系列跨界方式。也就是说,这里不仅呈现的是一个科创功能性空间,更要为科创人员提供一个多元、丰富、有趣,促进人与人邂逅、交流、思考、碰撞,激发创造灵感的环境。
这样的科创园区,在国内比较少见,但在国际上已经成为趋势。从某种角度说,全球科创,正逐渐“回归对人的尊重,满足人的需求”。
轻量化,回归“都市型社区”
从全球趋势看,科创街区的发展,可以粗略分为几个阶段。
第一阶段,依附于产业圈的配套型科创。早期的科创活动并非独立存在的,而是作为产业园区的“配套模块”嵌入其中。
彼时,创新需求高度依赖既有产业基础。比如在制造业集聚区周边,可能会有小型的研发中心、技术改造工作室。它们规模不大,功能单一,核心任务是对接产业端的具体需求。
这种“寄生式”的存在,让科创活动始终围绕产业圈的核心业务展开,缺乏独立的空间载体和发展逻辑,更像是产业体系延伸出的“创新触手”。
第二阶段,独立园区的规模化集聚。此时,科创活动逐渐摆脱对单一产业的依附,进入独立园区化发展的阶段。
以上海张江科学城为代表的创新型园区,是这一阶段的典型产物。它们往往选址在远郊或城市边缘区域,拥有独立的规划边界和配套体系,强调“大设施、大体量、高密度”的集聚效应——从国家级实验室到中试基地,从孵化平台到人才社区,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创新生态闭环。
这种布局的优势在于能集中配置稀缺的科研资源,降低创新主体间的协作成本,但同时也因地理上相对偏远,与城市核心功能区形成一定割裂。
第三阶段,轻量化渗透的都市化扩散。当下的“科创回归都市”,本质并非简单的地理空间回迁,而是创新活动本身的形态变革带来的空间重构。
随着人工智能、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崛起,科创活动呈现出显著的“轻量化”特征——一台笔记本电脑、一个研发团队,就能开展核心创新工作,不再依赖动辄数千平方米的实验场地或重型设备。
这种变化让创新载体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。它可能是市中心写字楼里的一个创业工位,也可能是老厂房改造的联合办公空间,甚至是社区里的共享实验室。
它们突出的优势是“短链条反馈”:从创意产生到原型验证,再到市场测试,能在城市肌理中快速完成闭环,与消费端、应用端形成即时互动。
这种分布式的存在,让科创活动真正融入都市生活,成为城市有机更新的“活力细胞”,也让创新不再受限于特定园区的边界,实现从“集中集聚”到“全域渗透”的质变。
正因为看到这样的变化,张江科学城内孕育的项目张江之尚,尝试在这方面破局。
自1988年北京中关村作为中国首个科技园区成立以来,在科创街区的发展中,我国已经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。
而上海,建设科创中心的过程中,诞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类街区。它们有的起初只是自发形成,有的来自自上而下的精心规划。
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相关研究人员表示,经过一系列调研和采访,概览上海科创街区,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五大模式。
第一种是高校驱动模式。以大零号湾为典型。高校不仅为周边科创街区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科研成果,其教学、生活也与城市的商业、居住、公共服务等功能深度交织,形成了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发展生态。
第二种是研究机构驱动模式。比如中国科学院下属的研究所,或是医院及其附属的医学研究室、科研中心。
以上海徐汇的枫林路街区为例,依托几家大型医院,整个街区聚集了大量生物医药企业。这些企业与医院形成了紧密的联动关系,在临床验证、技术研发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,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落地。
第三种是龙头企业驱动模式。初期通过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吸引上下游企业集聚,形成产业集群。从长期发展来看,这些龙头企业往往会超越单纯的企业角色,向开发运营主体转型。
以上3种模式有一个共同特征,即存在一个明确的核心机构,作为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。
第四种是环境与城市服务设施驱动模式。以上海西岸为例,它并非依靠单一的某个机构或资源,而是将整个西岸滨江地区打造成具有影响力的城区品牌。这里融合了文化、艺术、生活方式,相关技术人员喜欢西岸的年轻、潮流、艺术氛围,愿意在这里办公,从而吸引AI类产业和人群集聚。
这种模式的核心吸引力来自环境优势、完善的城市生活服务,注重场景共享,依托相对优越的区位条件。
第五种是成本优势驱动模式。该模式多存在于远郊或工业转型区域,比如宝山的部分区域。由于土地、厂房等成本相对较低,自然吸引了一些对成本敏感的企业入驻,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初期驱动力。
几位受访专家普遍认为,上海资源种类丰富,又囿于房地产成本高,在产业集聚上,很难形成杭州那样的特色小镇式的集中布局,实际上也没必要去做类似的“产业小镇”。
上海的每一栋楼宇中就可能孕育出多元的、集聚上下游产业的科创力量,每一个共享办公空间中就可能诞生创新成果转化。
上海看似没有科创类明星企业,实际上,在生物医药、高端装备等硬科技领域一直具备深厚实力,只是有些技术“不为互联网宣传”,未作为“明星企业”被广为人知。
“上海的优势在于产业配套完善、成果转化高效。科创的积累有厚度、有延展度。”一位长期观察科创领域的专家表示。
那么面向未来,适合上海的科创街区应该侧重什么呢?打造科创人员更喜欢的“都市型”创新街区——具备类似中心城区的生活、艺术、文化休闲氛围,具备为科创人群画像而定制的一系列激发灵感碰撞的环境。
在曾经被认为只有工业厂房、冰冷机器、钢筋水泥的科创园区里,把艺术、人文、生活放在突出位置。这是上海的一种尝试,或许也是大势所趋。
原标题:《为什么这样的街区,吸引科研人才》
作者:解放日报 龚丹韵
发布于:北京市涨8配资-个人场外配资-在线股票平台-最新实盘配资服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